张亚勤在云端:适者生存的新样板
张亚勤有篇文章叫做“未来计算在‘云端’”。“云端”是一个能让整个IT产业兴奋的词,有人说未来计算将由“端”走向“云”,最终全部集合到云中,成为纯“云”计算的时代。也有人说,“云-端”互动才是未来计算架构的发展趋势。这些技术趋势我们先按下不表,但是微软,这家PC时代的巨人,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公司,斥巨资在全球各地架设数据中心,构建了一个“在云端”的帝国。
张亚勤的身份是中国研发集团的主席,而最近,这家微软海外最大的研究机构升级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,涵盖除印度外的所有亚洲地区的微软研发团队。张亚勤说,这不过是自然发展。日本、韩国的研究团队早就向中国这边汇报了,再不更名有点“名不副实”。
《在云端》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,片中的乔治。克鲁尼饰演的是一名叫瑞恩。宾厄姆的公司裁员专家,他的工作是飞来飞去为各地公司去解决麻烦。
张亚勤也是个在“云端”的人。他经常飞来飞去穿梭于中美,只不过,他的任务不是裁员,而是沟通与交流,将正在和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产业趋势,汇报给他的mentor(导师),比尔。盖茨。
每个人进微软都可以选择一个“导师”,微软中国的员工喜欢称之为“馒头”,即mentor。让有经验的前辈成为后来者的教练,在技术、职业发展等各方面遇到疑惑时可以随时请教。于是当2004年张亚勤回到微软总部,同时升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时,他问盖茨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导师,盖茨同意了。
很显然,盖茨也很欣赏这个有“神童”光环的年轻人——他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,23岁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乔治。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,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,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,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。有媒体盛赞,他已经从“神童”走向了“神话”。他的博士导师瑞曼德。比克赫尔茨教授则感叹,“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!”
适者生存的新样板
事实上,张亚勤非常平易近人。在本刊为他拍照的间隙,他可以轻松地加入身边工作人员正讨论的话题中,比如高温瑜珈。他太太前段时间热衷于此,他便也跟着去练。他太太最近不去了,所以他的运动变成了和儿子一起打台球。
财经作家凌志军曾如此描绘张亚勤:他的外表浑圆忠厚,憨态可掬,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,举大体不论细节,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,总是能够一语中的。他的兴趣广泛,但却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。他常常一连数日闭门不出,沉浸在他的多媒体世界,但他也喜欢做生意,对风险投资和股票买卖都有兴趣,还喜欢下围棋,打球,玩扑克牌。
有人曾好奇他下巴上的两颗痣,是否就是天赋异禀的面相,张亚勤则坦言自己从未研究过,同时笑着展示出手掌中的第三颗痣。
在旁人的印象里,他是一个一帆风顺,平步青云的幸运儿,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“文革”开始的那一年,他才两岁,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。张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,家里忽然一团糟,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,他知道父亲死了。那一年他 5 岁,以这样的年龄,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,但他知道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而当张亚勤决定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后,每天20个小时的学习强度压倒了他的身体,在高考前他得了急性肝炎,不得不住院治疗。走出1978年那个黑色的7月,他的高考成绩比中科大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差了10分。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,张亚勤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他信心的信息——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,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。就这样,在第二场考试之后,张亚勤如愿以偿进入中科大,这一年,他12岁。
回忆这段“神童”经历,张亚勤说,“我觉得这东西发生了就发生了,对我来讲是有优势的,但我认为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”。在中科大的第一年,张亚勤认为“还是蛮苦的”。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诸多变化让这个少年有些不适应。进了大学,一下没人管了,张亚勤喜欢跑出去玩,也不去上课。他套用现在的流行语,开玩笑说,“张亚勤你妈妈喊你上课”。但他是个适应力极强的人,在及时的调整之后,他找到了自己的节奏。
8年之后他赴美读博,此间的艰难融入和努力适应不再赘述,单提他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发生的一个故事。就在张亚勤的毕业论文快完成时,他在一位日本访问教授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份日文专业杂志,上面刊发的论文标题和自己的竟然一模一样。距离毕业论文截止的时间越来越近,张亚勤只能从头做起。最后这篇论文成为乔治。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。
张亚勤的成长经历和职业规划,除了显示出让人惊叹的天才之外,还展露出他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。他从那个高呼“早出人才,快出人才”的充满紧迫感的时代走出,找到了一个从容的节奏。
在问到是否认为自己早熟时,他说了一段颇让人玩味的话:“性格是这样的,成熟的人永远都很成熟,幼稚的人永远都很幼稚,这是没有办法去变的。比如我现在碰到当时一起念书的同学,见5分钟发现和原来完全一样。最根本的东西永远不会变的,5岁之后就很少会变了。”
微软的中国基因
不管是年薪过亿的职业经理人唐骏,还是广大青年的人生导师李开复,再到现在NBA中国的掌门人陈永正,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——那就是微软人。
和很多身居高位,却不太为公众熟知的外企高管相比,微软中国的明星经理人出奇的多。这些人大都个性鲜明,敢做敢言。
张亚勤认为,这和微软的内部文化有很大关系。“微软鼓励大家的这种个性,鼓励把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,对个人的限制较少,而且包容性很强,你可以讲错话,干错事,这里能包容很多错误和失败。”
比尔。盖茨有时候会觉得,失败比成功更加值得珍惜,甚至还有些偏激地认为“成功是一个讨厌的教员,它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,它不是一位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可靠的向导”。
微软刚进入中国的时候,只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市场的中心,主要的业务是销售。唐骏是这块业务的佼佼者,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正是急速发展的销售业务所必须的。唐骏高调的行为方式更是带来不少助力。唐骏不止一次地说过,他的职业准则是“做人、做事,偶尔作秀”。唐骏领导下的微软中国,在销售方面,是微软全球惟一一个连续6个月创造历史最高销售纪录的公司。当微软深入中国,打算把中国上升为一个研发中心的时候,他们找到了李开复。
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,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,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、后来的微软公司副总裁里克。雷斯特所说, “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,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。”同时他又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,他的上级和下级都说他是一个好老板。更重要的是,他愿意回到中国。
在加入微软之前,李开复已经5次到中国,并且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,在高校学生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。李开复的父亲李天民曾是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地区的立法委员,1993年老人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,他做了一个梦。他在梦中来到水边,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,上面写着:中华之恋。还说,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,那就是再写一本书,书名叫做《中国人未来的希望》。
李开复景仰父亲为人,深受其影响,并把父亲遗传的对联“有容德乃大,无求品自高”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。1998年8 月 29 日,李开复举家搬回中国,随身带着 10000 磅的行李。这事成了美国华人圈中议论的话题,这位传奇人物的归国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向他靠拢。李开复坦言,“这个决定对后来的结果还是很重要的。”
张亚勤正是被李开复邀请回国的。同李开复一样,张亚勤也一直有回国的念头。他的博士导师瑞曼德曾说,“亚勤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他对祖国怀有很深的感情,而且知恩图报。他以前经常说,要回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”
1999年1月,张亚勤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。一年以后,他接替李开复,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。
而现在,从市场中心和研发中心的阶段走过,中国日益重要,成为了微软的战略中心。张亚勤表示,中国就好像是微软的第二总部一样,职能部门非常齐全。“现在在做决策之前,中国是一个重要因素。每个决策者都要做一份美国的战略,一份中国的战略,还有一份全球的战略。就像解方程一样,中国变成了核心函数。”中国还是微软惟一一个有两个全球副总裁的大区。
而微软在中国的管理也日渐成熟,2008年11月微软宣布大中华区成立四人战略决策委员会,现在这个委员会已变成7人,把人事、财务都放进去了。张亚勤表示,在这个平台上,大家讨论一些事情,可以互相配合,做决策更加全面一些。
微软中国的成熟还表现在总部对中国的日渐理解上。每当中国有大事发生,比如两会、十七大时,张亚勤都会向比尔。盖茨和鲍尔默进行“洗脑”。他会把一些振兴计划和自主创新用很精练的语言讲给他们听。微软的一个CTO克瑞格。蒙迪(Craig Mundie)还把十七大报告的英文翻译版通读一遍,去中央党校谈自己的看法和理解。张亚勤笑言,“他们对中国越来越了解了,我就比较不累了”。
张亚勤表示微软就不会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,“我们也会犯错,但不会犯这些幼稚的错误”。张亚勤还在微博(http://t.sina.com.cn)中写,一个成熟的企业不可意气用事,要能经历磨难有长远眼光。中国是微软全球战略要地,是在美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创新基地。不管别的企业怎么做,微软已经深深融入中国。
更加“柔软”的微软
微软在2009年动作频出:发布PC操作系统Windows 7,发布手机操作系统Windows Mobile 6.5,推出搜索引擎Bing。这个昔日软件业的巨人开始和新时代的宠儿Google、苹果全线交战。
在PC时代“一家独大”的微软需要变得更加“柔软”,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的合作伙伴。不管是在云计算,还是在终端或者搜索领域,每一个大企业都无法通吃所有的业务,合作和融合是大势所趋。
比如在搜索领域。微软曾经走了一些弯路。最开始微软只把搜索当做是一种技术,没有上升到未来战略的高度。
唐骏在采访中表示,微软在搜索方面彻底没有优势。无论从技术层面,还是用户习惯,还是先入为主方面,微软都不具备太大的优势在里面。原来微软不怕,因为是产品的公司,只要不断地把产品做好,总有一天把对手打败。但是互联网不是产品,是一种服务。要做好服务很难,必须要靠商业模式的创新。
于是,微软后来采取的策略就是“合纵连横”。通过和Yahoo达成合作协议,两家加起来有近30%的市场份额,相比Bing的10%有了一定的话语权。
再比如移动平台上,微软也没能及时占领优势地位。2009年推出的Windows Mobile 6.5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成功。鉴于此,微软希望即将发布的Windows Mobile7能扭转颓势。
张亚勤曾经在2004年回到微软总部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,开拓Windows Mobile项目。
在这方面,微软最大的优势在业务模式方面——微软只做平台,不做手机,不做运营。一开始可能会慢一点,但是这样可以把整个产业链带动起来。这种合作的姿态也显露出一个更加“柔软”的微软。
而且还可以借助微软其他方面的优势。同是Windows平台,手机和电脑的信息可以更好的同步和兼容。再加上微软在这方面投入的人才和过去多年的积累,张亚勤相信在长期会有优势。
谈到微软的“个性”,张亚勤说,微软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公司。认定以后有前景的产业,会以很大的耐心来做,不会因为几年不盈利就放弃。有的时候速度不一定快,也不一定是第一个,但是很有韧性。就像微软当初选择进入家用游戏机市场,做Xbox.Xbox在美国上市时,PS2的全球销量已经突破了 2000万台,但微软还是后来居上。
比尔。盖茨在40岁之时成为世界首富,他创办的微软那时成立刚满20年。有财经作家评价,人家都说这个年轻的公司是电脑行业的“巨无霸”,但它自己却没有一点大企业的特征——沉稳、老练、步步为营、按部就班、等级森严和老谋深算,好像一个蹒跚挪步的老人。这个“巨无霸”倒像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,充满活力和幻想,喜怒无常,藐视规则,行事卤莽,横冲直撞。
张亚勤表示,现在的微软相比10年前,已经成熟很多。张亚勤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完美——1/3时间是对外,各种会议、沟通,和政府、媒体、客户,包括和美国方面;1/3完全是自己在看东西,读论文,写东西;还有1/3是内部的管理。张亚勤笑言,自己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忙。“如果很清楚怎么做,找到合适的团队,清楚的战略,很多事情你都不用做”。
试图变得更加“柔软”的微软,正需要张亚勤这种同样“个性柔软”、适应力强的人物,去将其开放与合作的理念,与外界分享,从而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收获。看来,张亚勤在微软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。
张亚勤的身份是中国研发集团的主席,而最近,这家微软海外最大的研究机构升级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,涵盖除印度外的所有亚洲地区的微软研发团队。张亚勤说,这不过是自然发展。日本、韩国的研究团队早就向中国这边汇报了,再不更名有点“名不副实”。
《在云端》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部电影,片中的乔治。克鲁尼饰演的是一名叫瑞恩。宾厄姆的公司裁员专家,他的工作是飞来飞去为各地公司去解决麻烦。
张亚勤也是个在“云端”的人。他经常飞来飞去穿梭于中美,只不过,他的任务不是裁员,而是沟通与交流,将正在和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产业趋势,汇报给他的mentor(导师),比尔。盖茨。
每个人进微软都可以选择一个“导师”,微软中国的员工喜欢称之为“馒头”,即mentor。让有经验的前辈成为后来者的教练,在技术、职业发展等各方面遇到疑惑时可以随时请教。于是当2004年张亚勤回到微软总部,同时升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时,他问盖茨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导师,盖茨同意了。
很显然,盖茨也很欣赏这个有“神童”光环的年轻人——他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,23岁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乔治。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,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,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,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。有媒体盛赞,他已经从“神童”走向了“神话”。他的博士导师瑞曼德。比克赫尔茨教授则感叹,“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!”
适者生存的新样板
事实上,张亚勤非常平易近人。在本刊为他拍照的间隙,他可以轻松地加入身边工作人员正讨论的话题中,比如高温瑜珈。他太太前段时间热衷于此,他便也跟着去练。他太太最近不去了,所以他的运动变成了和儿子一起打台球。
财经作家凌志军曾如此描绘张亚勤:他的外表浑圆忠厚,憨态可掬,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,举大体不论细节,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,总是能够一语中的。他的兴趣广泛,但却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。他常常一连数日闭门不出,沉浸在他的多媒体世界,但他也喜欢做生意,对风险投资和股票买卖都有兴趣,还喜欢下围棋,打球,玩扑克牌。
有人曾好奇他下巴上的两颗痣,是否就是天赋异禀的面相,张亚勤则坦言自己从未研究过,同时笑着展示出手掌中的第三颗痣。
在旁人的印象里,他是一个一帆风顺,平步青云的幸运儿,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“文革”开始的那一年,他才两岁,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。张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,家里忽然一团糟,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,他知道父亲死了。那一年他 5 岁,以这样的年龄,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,但他知道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而当张亚勤决定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后,每天20个小时的学习强度压倒了他的身体,在高考前他得了急性肝炎,不得不住院治疗。走出1978年那个黑色的7月,他的高考成绩比中科大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差了10分。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,张亚勤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他信心的信息——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,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。就这样,在第二场考试之后,张亚勤如愿以偿进入中科大,这一年,他12岁。
回忆这段“神童”经历,张亚勤说,“我觉得这东西发生了就发生了,对我来讲是有优势的,但我认为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”。在中科大的第一年,张亚勤认为“还是蛮苦的”。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诸多变化让这个少年有些不适应。进了大学,一下没人管了,张亚勤喜欢跑出去玩,也不去上课。他套用现在的流行语,开玩笑说,“张亚勤你妈妈喊你上课”。但他是个适应力极强的人,在及时的调整之后,他找到了自己的节奏。
8年之后他赴美读博,此间的艰难融入和努力适应不再赘述,单提他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发生的一个故事。就在张亚勤的毕业论文快完成时,他在一位日本访问教授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份日文专业杂志,上面刊发的论文标题和自己的竟然一模一样。距离毕业论文截止的时间越来越近,张亚勤只能从头做起。最后这篇论文成为乔治。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。
张亚勤的成长经历和职业规划,除了显示出让人惊叹的天才之外,还展露出他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。他从那个高呼“早出人才,快出人才”的充满紧迫感的时代走出,找到了一个从容的节奏。
在问到是否认为自己早熟时,他说了一段颇让人玩味的话:“性格是这样的,成熟的人永远都很成熟,幼稚的人永远都很幼稚,这是没有办法去变的。比如我现在碰到当时一起念书的同学,见5分钟发现和原来完全一样。最根本的东西永远不会变的,5岁之后就很少会变了。”
微软的中国基因
不管是年薪过亿的职业经理人唐骏,还是广大青年的人生导师李开复,再到现在NBA中国的掌门人陈永正,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——那就是微软人。
和很多身居高位,却不太为公众熟知的外企高管相比,微软中国的明星经理人出奇的多。这些人大都个性鲜明,敢做敢言。
张亚勤认为,这和微软的内部文化有很大关系。“微软鼓励大家的这种个性,鼓励把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,对个人的限制较少,而且包容性很强,你可以讲错话,干错事,这里能包容很多错误和失败。”
比尔。盖茨有时候会觉得,失败比成功更加值得珍惜,甚至还有些偏激地认为“成功是一个讨厌的教员,它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,它不是一位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可靠的向导”。
微软刚进入中国的时候,只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市场的中心,主要的业务是销售。唐骏是这块业务的佼佼者,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正是急速发展的销售业务所必须的。唐骏高调的行为方式更是带来不少助力。唐骏不止一次地说过,他的职业准则是“做人、做事,偶尔作秀”。唐骏领导下的微软中国,在销售方面,是微软全球惟一一个连续6个月创造历史最高销售纪录的公司。当微软深入中国,打算把中国上升为一个研发中心的时候,他们找到了李开复。
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,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,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、后来的微软公司副总裁里克。雷斯特所说, “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,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。”同时他又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,他的上级和下级都说他是一个好老板。更重要的是,他愿意回到中国。
在加入微软之前,李开复已经5次到中国,并且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,在高校学生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。李开复的父亲李天民曾是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地区的立法委员,1993年老人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,他做了一个梦。他在梦中来到水边,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,上面写着:中华之恋。还说,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,那就是再写一本书,书名叫做《中国人未来的希望》。
李开复景仰父亲为人,深受其影响,并把父亲遗传的对联“有容德乃大,无求品自高”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。1998年8 月 29 日,李开复举家搬回中国,随身带着 10000 磅的行李。这事成了美国华人圈中议论的话题,这位传奇人物的归国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向他靠拢。李开复坦言,“这个决定对后来的结果还是很重要的。”
张亚勤正是被李开复邀请回国的。同李开复一样,张亚勤也一直有回国的念头。他的博士导师瑞曼德曾说,“亚勤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他对祖国怀有很深的感情,而且知恩图报。他以前经常说,要回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”
1999年1月,张亚勤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。一年以后,他接替李开复,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。
而现在,从市场中心和研发中心的阶段走过,中国日益重要,成为了微软的战略中心。张亚勤表示,中国就好像是微软的第二总部一样,职能部门非常齐全。“现在在做决策之前,中国是一个重要因素。每个决策者都要做一份美国的战略,一份中国的战略,还有一份全球的战略。就像解方程一样,中国变成了核心函数。”中国还是微软惟一一个有两个全球副总裁的大区。
而微软在中国的管理也日渐成熟,2008年11月微软宣布大中华区成立四人战略决策委员会,现在这个委员会已变成7人,把人事、财务都放进去了。张亚勤表示,在这个平台上,大家讨论一些事情,可以互相配合,做决策更加全面一些。
微软中国的成熟还表现在总部对中国的日渐理解上。每当中国有大事发生,比如两会、十七大时,张亚勤都会向比尔。盖茨和鲍尔默进行“洗脑”。他会把一些振兴计划和自主创新用很精练的语言讲给他们听。微软的一个CTO克瑞格。蒙迪(Craig Mundie)还把十七大报告的英文翻译版通读一遍,去中央党校谈自己的看法和理解。张亚勤笑言,“他们对中国越来越了解了,我就比较不累了”。
张亚勤表示微软就不会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,“我们也会犯错,但不会犯这些幼稚的错误”。张亚勤还在微博(http://t.sina.com.cn)中写,一个成熟的企业不可意气用事,要能经历磨难有长远眼光。中国是微软全球战略要地,是在美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创新基地。不管别的企业怎么做,微软已经深深融入中国。
更加“柔软”的微软
微软在2009年动作频出:发布PC操作系统Windows 7,发布手机操作系统Windows Mobile 6.5,推出搜索引擎Bing。这个昔日软件业的巨人开始和新时代的宠儿Google、苹果全线交战。
在PC时代“一家独大”的微软需要变得更加“柔软”,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更多的合作伙伴。不管是在云计算,还是在终端或者搜索领域,每一个大企业都无法通吃所有的业务,合作和融合是大势所趋。
比如在搜索领域。微软曾经走了一些弯路。最开始微软只把搜索当做是一种技术,没有上升到未来战略的高度。
唐骏在采访中表示,微软在搜索方面彻底没有优势。无论从技术层面,还是用户习惯,还是先入为主方面,微软都不具备太大的优势在里面。原来微软不怕,因为是产品的公司,只要不断地把产品做好,总有一天把对手打败。但是互联网不是产品,是一种服务。要做好服务很难,必须要靠商业模式的创新。
于是,微软后来采取的策略就是“合纵连横”。通过和Yahoo达成合作协议,两家加起来有近30%的市场份额,相比Bing的10%有了一定的话语权。
再比如移动平台上,微软也没能及时占领优势地位。2009年推出的Windows Mobile 6.5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成功。鉴于此,微软希望即将发布的Windows Mobile7能扭转颓势。
张亚勤曾经在2004年回到微软总部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,开拓Windows Mobile项目。
在这方面,微软最大的优势在业务模式方面——微软只做平台,不做手机,不做运营。一开始可能会慢一点,但是这样可以把整个产业链带动起来。这种合作的姿态也显露出一个更加“柔软”的微软。
而且还可以借助微软其他方面的优势。同是Windows平台,手机和电脑的信息可以更好的同步和兼容。再加上微软在这方面投入的人才和过去多年的积累,张亚勤相信在长期会有优势。
谈到微软的“个性”,张亚勤说,微软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公司。认定以后有前景的产业,会以很大的耐心来做,不会因为几年不盈利就放弃。有的时候速度不一定快,也不一定是第一个,但是很有韧性。就像微软当初选择进入家用游戏机市场,做Xbox.Xbox在美国上市时,PS2的全球销量已经突破了 2000万台,但微软还是后来居上。
比尔。盖茨在40岁之时成为世界首富,他创办的微软那时成立刚满20年。有财经作家评价,人家都说这个年轻的公司是电脑行业的“巨无霸”,但它自己却没有一点大企业的特征——沉稳、老练、步步为营、按部就班、等级森严和老谋深算,好像一个蹒跚挪步的老人。这个“巨无霸”倒像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,充满活力和幻想,喜怒无常,藐视规则,行事卤莽,横冲直撞。
张亚勤表示,现在的微软相比10年前,已经成熟很多。张亚勤现在的工作状态非常完美——1/3时间是对外,各种会议、沟通,和政府、媒体、客户,包括和美国方面;1/3完全是自己在看东西,读论文,写东西;还有1/3是内部的管理。张亚勤笑言,自己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忙。“如果很清楚怎么做,找到合适的团队,清楚的战略,很多事情你都不用做”。
试图变得更加“柔软”的微软,正需要张亚勤这种同样“个性柔软”、适应力强的人物,去将其开放与合作的理念,与外界分享,从而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收获。看来,张亚勤在微软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。

来源:东方企业家
#云端#
#张亚勤#
#样板#
#适者生存#
THE END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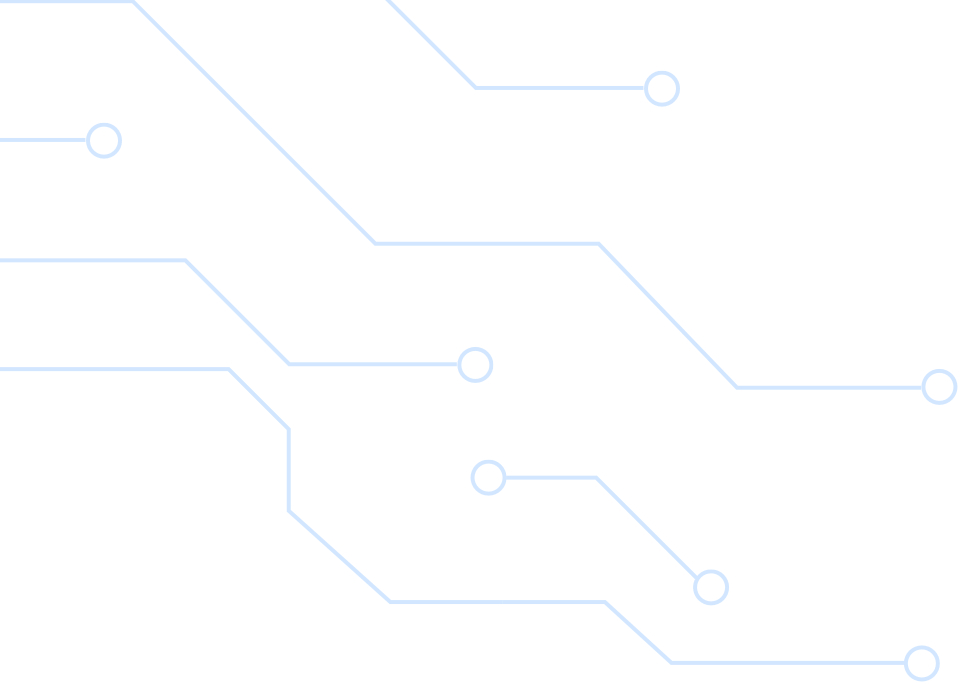






评论
文明上网理性发言,请遵守新闻评论服务协议
登录参与评论
0/1000